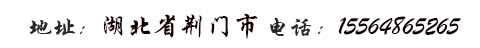广州番禺作别南沙,归来仍是英姿勃发的
| 叁崛起于明、清明清之时,虽然海水已逐渐向南退去,但因珠江河道在珠江三角洲分成多条,大谷围仍悬于茫茫水域中,出入仅靠水路。水能围困大谷围,也能造福大谷围。这里人们以非凡的智慧,充分利用水所形成的劳作、交通等便利,由此促成了大谷围在明清两朝的迅猛崛起。市桥水道与紫坭河交汇。那个时候,珠江两岸人们的致富路径是不同的:广州府城依靠贸易而兴盛,珠江北岸的禺北(为慕德里司所辖,地域为今白云区的南岗、太和、龙归、良田、竹料、钟落潭、鸦湖、蚌湖、嘉禾、神山、江村、石井、江高等),有白云山等丘陵,山多而平地少,以农耕为主;禺东(为鹿步司所辖,包括今黄埔的大部分,天河区的大部分,以及白云区的大源、同和等)的北部也是农耕区,南部因近珠江,有一定的渔业资源,且有港口,商业较发达。相比之下,面向南海的大谷围与同县的禺北、禺东兄弟不同,它既有水路利于经商,又有大面积的河沙冲积形成的围田,以及快速聚集财富的“核武”——沙田拓殖的便利,当然还有远比禺东南部近珠江水域更加优渥的渔业条件。这些天然的优势,使经济方式多样化成为可能,让围上那些既务实又能盘算的广府人家积累下厚实的家底,一些大家族出现了,乡村的风貌也在悄然改善。大谷围田地类型多样,又有天赐的充足热量和雨量,所以田间地头的出产甚丰,一年之间,水稻两熟;杂粮蔬果,随时可种。这里出产的大宗农产品,包括水稻、蔬菜(如适应本地环境的雍菜)、水果等。后者包括荔枝、龙眼、橄榄等,又以荔枝闻名。《广东新语》有载:“水枝以黑叶为上,黑叶又以番禺古坝所产为上……番禺之韦涌次之。”这里濒江临海,有池塘、内河、大海等适宜渔业的资源,出产丰富,河鲜有鲢、鳙、鲩、鲶、鲫、鲤等,海鲜则有鱼、虾、蟹、贝类等。因地处咸淡水交汇处,蚝产闻名。这是同样有渔业的鹿步司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就生产情形看,若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这里有一些村落经营着一些特别的产业,比如大岭村,除了民田和沙田外,还充分利用村周的岗地发展林业。又如曾边村等地,明清时仍烧窑不止。这些产业是当地人致富的有益补充。但农业仍是大谷围的定鼎基业,为围中的人们积累下丰厚的财富。这些品种众多,数量丰富的产品资源,最终通过围外的珠江后航道、虎门水道、沙湾水道等水路,销往他处。为适应的交易的需要,一些墟市出现了。据明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当时番禺城外的5个巡检司共有9个墟市,在大谷围的就有新造、菱塘、沙湾3个(分属菱塘巡检司和沙湾巡检司),数量最多。后来,乡村市场不断增加。如清代前期,沙湾巡检司下辖墟市达15个,到了清代中后期,发展到17个,至清末则达25个,这是经济繁荣的见证。诸如蔡边墟、古坝墟、傍江墟、韦涌墟、紫泥墟、官塘墟、南村墟、明经墟、赤沙墟等,则从清初一路发展到民国时期而未见衰落。这些沿河或沿街设置的墟市,是人们互换有无的交易中心。比如市桥市,交通便利,人民富裕,商店逾千,附近各乡人常来往这里。又如菱塘墟,《广东新语·地语》说“菱塘之地濒海,凡朝虚(即“墟”,笔者注)夕市,贩夫贩妇,各以其所捕海鲜连筐而至。农家之所有,则以钱易之。蛋人(即“疍人”,笔者注)之所有,则以米易之。”这众多的墟市,成为大谷围人民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清代以后,广州“一口通商”,沙湾巡检司辖地还设有两个对外贸易所需的挂号口,即市桥口和紫泥口,又成为大谷围与外界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沙湾古镇全貌人流与财富的集聚,促成了街市的繁华。而发达的手工业(如清末市桥的晒染业),以及农业向商业的快速转化,农商一体化的经济特征已很明显。如此高度的经济发展,也促成了与之匹配的经济载体,即市镇的产生,这些市镇多近河岸,如在市桥水道边的市桥、位居紫坭河和顺德水道间的紫泥、在珠江后航道南岸的新造等。随之而来的,则是文化交流和社会交流的汇集。大谷围城镇的肌理,因而越来越清晰。到了清末民初,市桥成为沙湾巡检司的商业中心,新造则为菱塘巡检司的商业中心,大石墟、员岗墟发展为早晚皆市的大石市、员岗市。但大谷围的异军突起,除了上述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沙田拓殖。大谷围上那些大族,无一例外地都从中获益。资料显示,沙田在大谷围内外分布广泛,包括石碁、沙湾、石楼所属部分,今天属于南沙的黄阁、东涌、榄核、横沥的全部,都是原来的沙田区,是商品粮和糖蔗、香蕉、大蕉等的生产基地。这些沙田当地方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清末,市桥作为沙湾司唯一的产糖基地,每年的糖产量位居番禺县第一。与顺德、新会、南海等地的沙田一样,这里的沙田也几乎被那些自宋、元、明以来定居在大谷围内岗丘台地上的大姓(宗族组织形成后则为宗族,一些学者称之为“豪右”“著姓右族”)势力所控制,如沙湾的何氏、员岗的崔氏、南村的邬氏、石楼的陈氏、大石的何氏等。原来以渔业为生的疍民成为沙田的主要劳动力,一些无地的贫民也闻风而来,租种沙田。沙田拓殖,除了农业的增收,还有沙田下“蚝矿”(即成带状分布的蚝壳。当时,从今天天河的猎德至虎门的珠江沿岸,蚝壳大量分布)的开采。这些蚝矿极大,比如茭塘村,史载这里“掘地至二三尺即得蚝壳,多不可穷”。民国《番禺县续志》记载这里的蚝壳矿“相叠成山,蔓延甚广。”蚝壳可建屋,可炼蚝壳灰替代石灰成为建筑材料,同样可给沙田开发者带来丰厚的收入。顺带说一下,榄核镇之名,就与采蚝壳有关。据说当时采壳的人们将挖出的沙泥堆积在滩涂上,这些泥堆被水流冲刷,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榄核形,因此有了“榄核”之名。沙湾,蚝壳屋外墙因有控制权,沙田成为那些大姓宗族的提款机。其中的一些家族,如沙湾何族控制的沙田面积达五六万亩,另外的一些家族,占有的沙田也是几千至数万亩不等。沙田开发的收入有多丰厚?以沙湾何氏宗族为例,在清代中期以后,仅是留耕堂的族产,每年可收成谷物达数百万斤!根据当地人的回忆,何氏留耕堂以及各房的公尝,每年都会向族内男丁分发数十斤猪肉以及一笔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现金。且何氏一族成员从出生、婚娶到丧葬,以及入学、科举考试,都可获得资助。这与如今广州市域中那些每年按股分红的村落没什么两样。如果还想看看当时这些宗族富得流油的自得模样,那么,可以走进沙湾古镇、员岗古村、大岭古村看看,那些由无数青石铺就的条条整洁的大街小巷,以及恢宏得近似炫耀的祠堂。无疑,它们都有沙田的巨大贡献。因沙田致富,还有一些值得一说的细节。记得田野体验时,在员岗村的高峰崔公祠,守护祠堂的一位崔氏族人很是自豪地说:解放前,村内通往农田的道路都是用青石铺就的。他还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建造高峰崔公祠时,主持修建的祖上要求工匠一天只许铺一片地砖,故意让宗祠延时建成,以此炫富。这些是否属实,已难以查证,但崔氏族人从沙田中获得了巨额收入,从中可窥一斑。当时,当地还流传着俗语:“十日四墟朝晚市,有女唔嫁员岗等几时。”说的也是员岗的繁华。沙田拓殖带来的巨额收入,又带动人们经营其他行业,如沙湾有人把店铺开到了顺德陈村,罗边的罗氏到省城开起了钱庄……很多家族因此富上加富。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叙说。由于经济的富足,无论大姓还是小姓宗族,纷纷建起了祠堂。至清代,大谷围上的每座村落几乎都建起了祠堂,且无论大姓之族或是小姓单家,都会立宗祠代为堂构。像居于沙湾的何、王、李、黎、赵五大姓,就建有超过座宗族祠堂,各姓均有一座至数十座不等。同时,他们还加大力度反哺族人的教育之业,广建家塾、书院等教育机构,立文武庙等助文运之兴的建筑,营造浓郁的教育及教化氛围,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南下中原人的传统发扬光大,大谷围的文教也因此而云蒸霞蔚。大岭村显宗祠明代中叶以后,这里参加科举考试且取得功名者众多,科名鼎甲的家族也不断涌现。大岭陈氏家族、员岗崔氏家族、沙湾的王氏家族与何氏家族、韦涌的方氏家族、石楼陈氏家族、市桥谢氏家族、大石何氏家族、南村邬氏家族、古坝韩氏家族等都是当地以科第显的望族。考取功名者,最盛的大族是沙湾何氏,在明清两代,出过进士(包括武进士)7名,举人(包括武举人)35名;石楼陈氏家族也不示弱,出进士5人,举人23人;大岭陈氏则出进士5名,举人14名;大石何氏出进士4人;员岗崔氏有进士3名,举人36名……就科考而言,取得功名的人数从乾隆以后不断上升,到光绪年间攀至高峰。根据统计,在光绪年间,大谷围文人考取进士者超过30人。同期的禺东和禺北地区取得进士功名者,则不到10人(禺东萝岗钟狮、猎德林诞禹,禺北的南岗周日新、周汝钧,大田谢銮波等)。各大家族虽有竞争,但也通过联姻而实现强强联合;内部时有刀来剑往,但也有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光荣时刻。那些取得功名的出仕者,也多对家乡有所帮扶。这是大谷围人得以安居乐业之幸事。莘汀村家塾同时,包括秀才在内的大批文人通过社学、私塾、书院等实现文化的薪火相传,又广开诗社与文会,这里形成了优良文风,史载“番禺士尚儒雅,重才华……”杰出者如屈大均(莘汀村人),著有《广东新语》。因着文化的影响,大谷围的民俗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紫泥春色、市桥水色、沙湾飘色、员岗飘色、“十乡会”会景巡游、广东音乐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此,大谷围的文化景观已和禺北、禺南甚至是广州城趋于一致。但就经济而言,它后来居上,完成了对禺北和禺南的超越。这也是解放前夕大谷围地方乡绅谋划建立“禺南县”的重要原因。那个时候的番禺可与南海、顺德并称“南番顺”,大谷围功不可没。肆从“睡城”中醒来年后,番禺县归属与地域在不断的调整中,直到年才稳定下来。在这样的大气候影响下,大谷围地域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不愠不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南海、顺德成了“广东四小虎”的成员,而大谷围所在的番禺,则被远远抛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谷围以种植粮、蔗为主,兼有鱼塘养殖业,开门即是田野、山岗,鲜见工业区。年,这里开始了建设的热潮。几年后,钟村佛子岭周边的沼泽荒地,也热闹起来,番禺超大楼盘的时代,在这里拉开帷幕,番禺超大楼盘的始祖,号称“中国第一邨”的祈福新村(邨),已呼之欲出。日后“睡城”印象的形成,它是“肇事者”。华南新城一角进入21世纪,番禺撤市建区,成为广州南拓的重点。这个时候,连接市区与番禺的华南快速干线业已开通,大谷围西部的地产不断升温。年4月,位于华南快速干线的番禺大桥脚下的星河湾开盘;5月,华南碧桂园开盘。随后,南国奥林匹克花园、锦绣香江、华南新城、广州雅居乐、广地花园相继落子于此。极具地产色彩的“华南板块”也开始叫响。因为这些楼盘的面积无一例外的大,如祈福新村,面积5平方千米;广州雅居乐,面积3.2平方千米;华南新城,面积2.1平方千米;甚至最小的华南碧桂园都有0.27平方千米。这些楼盘宣告了中国地产的“大盘时代”来临。这些楼盘的的主人,是大量的“广漂”们。作为新广州人,他们晚上在这里休息,白天则到广州城区上班,这导致洛溪大桥、番禺大桥、新光快速上由南往北的车流不息,如遇塞车,可达千米之长。“睡城”之名由此而起。一定程度上,这些扎根于钟村、南浦、大石等地的大盘,扩散了原本局限于市桥的繁华。但它们也占据了大量的战略性土地资源,让原本可沿广州大道、新光快速南拓至番禺市桥的路径受阻。如若不改变这种格局,“睡城”之名将难以消除。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迟来的城市规划者不得不重新布局。他们将眼光移到大谷围的东部,以此打造新的南拓之路,于是,地铁4号线、南沙港快线、新化快速路、广州绕城高速东段等交通干线上马,串联起科学城、琶洲会展中心、生物岛、大学城、亚运城、南沙港区等,另再建地铁18号线、22号线实现番禺与广州城北、城西的联通。在围内,连接围东与围西的亚运大道、广台高速、南大干线等的相继建成,不同区位的均衡发展有了保证。同时,人们还沿着这些交通线不断更新与优化产业布局,形成广州南站商务区、长隆旅游度假区、广州亚运城、万博CBD、广州巨大创意产业园(位于大石)、番禺汽车城(位于化龙和石楼)、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位于化龙)、思科(广州)智慧城(位于新造)、沙湾珠宝产业园(位于沙湾)、星力动漫游戏产业园(位于东环街)、番禺节能科技园(位于东环街)、金山谷意库(位于东环街)、海伦堡创意园(沙头街)等产业集群区,其中还有多个村级工业园。这些更新了大谷围的产业格局,多元化的支点将帮助番禺夺回发展的主动权,助力大谷围再次迎来属于她的荣耀时刻。后记: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感觉“番禺”这个政区名称能保留至今实属幸运。历史上,这个名字有3次被弃用的危险:年的时候,当地乡绅谋划成立“禺南县”;年以番禺县南部和顺德县合并置番顺县;-年间,有人提出让南沙“吞并”番禺。幸好,都是虚惊一场。但按此趋势,谁又能保证它能延续下去?一个存续了多年的名字,历史价值赋存其中。在拿掉它之前,那个主张者须细细掂量。今天,“番禺”之名下的地域面积已是历史最小,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广州目前的11个区中,它仍排在第六位,而且文化底蕴不输其他,更非南沙能比。过去,大谷围人抓住海退之机,利用沙田而致富,名震一方。今天,番禺人能否借助科技、文化之兴,再造创富的新“沙田”?答案已写在春秋里。期待未来的番禺,科技如幻,商业繁荣,是南来北往车骑停歇之地。同时更宜居,花草铺地,四季如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shacan.com/nsszy/12531.html
- 上一篇文章: 瑞丽喊沙村云南旅游中国十大最美丽的村庄
- 下一篇文章: 永暑岛竟然有大量淡水,南沙吹沙填海是